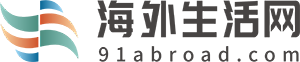世界快看點丨新銳小說家張玲玲:小說在當下面臨多樣競爭|封面專訪
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在短視頻風行、視頻圖像越來越成為主流信息形式的當下,尤其是強人工智能在創意類工種領域表現“震驚”世界的語境下,還有年輕人全職投身到嚴肅文學或曰純文學的創作中,不能不說是一種罕見的勇氣。
張玲玲1986年生于江蘇,曾當過7年財經記者,做過影視編劇,如今她專注寫小說,2019年出版小說集《嫉妒》備受矚目,進入由蘇童、孫甘露、西川等名家擔任專業評審的2020年第三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評獎長名單。2023年6月,張玲玲又一部小說集《夜櫻與四季》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再次引發業內關注。
 (相關資料圖)
(相關資料圖)
《夜櫻與四季》封面
以女性視角寫出當代青年心靈生活
書名《夜櫻與四季》來源于其中收錄的兩篇小說《夜櫻》與《四季歌》。其中《夜櫻》一篇首發于《小說界》2021年第1期,主題為“雪國”。在這部小說集中,張玲玲用她詩意的語言,流暢的故事講述能力,為我們展現出一幕幕耐人尋味的生活世界:暮春的上海,在天臺上和人爭論自己劇本的戲劇系女大學生;夏季山洪過后來鎮上尋找愛人,卻決定與之分手的女人;越來越濃的秋意里,執著想要找回失蹤丈夫的外來船員的妻子;冬日龐大的北方城市,選擇放棄過往,獨自面對絕癥父親的女兒。時間推移,年代流轉,帶來了她們生活和命運的轉變。在其中,女性的身影尤為突出:她們的回憶,她們的行動,她們隱藏起來的過往,形成這本小說集豐沛的情感張力,也匯聚成當下的時代聲音。
北師大文學院教授、資深文學批評家張莉看完這部小說給出這樣的讀后感,“流動的、飄忽不定的生存狀態是張玲玲小說的背景,也是她所凝視的生活狀態。輕盈、誠摯而深具真實感,她以一種獨特的女性視角寫出了當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心靈生活。 ”
對年代的敏感是很多優秀寫作者具備的鮮明特質,張玲玲也不例外。2010-2020年這十年,就在離我們不遠的昨天,如今已成為《夜櫻與四季》的時間背景,成為文學的書寫。張玲玲坦言,這十年變化很快,一開始會對這種變化感到震驚,但也會慢慢接受這種變化,“這種消失,這種突兀的,急遽的,新事物不停到來的感覺。然后它們又會很快變舊,消失。”這種對時間的感受,也融入到她的小說文本之中。
在諸多文本體裁之中,講一個精彩的故事,并不是文學類作品最首先或者核心的功能。如果想要讀一個好看的故事,在類型文學或者情感類網紅博主那里都可以得到滿足。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歸根結底還得在語言藝術上有自己鮮明的個人面貌。張玲玲的小說讀起來,語調鏗鏘,氣息綿長,稱得上是一個詩意的文本。
張玲玲(圖據受訪者)
從財經記者、影視編劇轉型專職寫小說
跟不少作家都有過一段媒體工作經歷一樣,張玲玲也曾經是一名記者。從新聞轉向文學,她自言“其實較為常規,甚至可能是85后寫作者的常規履歷。我們這批寫作者,和自新概念作文大賽走出的八零初作者有別,大部分都到30歲之后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第二、第三本之后,才逐步開啟全職作者之路。當然,也有許多人迄今未脫離工作。寫作并非忽然開始,多數人在高中、大學即有了一定的寫作嘗試,只是未能拿出,未成氣候,或者未被看見。但這些寫作嘗試或偏好可能導致你在職業選擇時,但凡有機會,都會選媒體、出版或企業、機關內的文宣等相關行業,因為它們離寫更近。”
張玲玲進入媒體行業是在2010年左右。大概六七年之后,影視熱錢涌動,視頻平臺的興起和競爭催生了大量的內容需求,一些媒體從業者也流到相關行業中去,其中也包括張玲玲。回憶這段經歷,她說,“抑制了真正的愿望去做了很多別的事,而不是愿望在工作里滋生、清晰。但這樣說也不公正,因為這段履歷其實教會了我很多。”
對話張玲玲
“小說敘述速度跟呼吸接近,情節推進又跟心跳相關”
封面新聞:在我的閱讀感受里,你的小說語言是沉靜、低沉的,像大提琴的音色,也很像你這部小說集的名字《夜櫻與四季》這兩個詞語的風格。而且你的小說語言在推進情節進展的時候,也比較簡練,不拖泥帶水。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小說文字表達調子的?
張玲玲:非常感謝您的細讀。小說的敘述速度跟你的呼吸接近,而情節推進又跟心跳相關。有時你修改,就是為了趨近你在最安靜時聽到的聲音,這個聲音既像你,又和日常的你存在較大差異。我也在閱讀里學習,在聆聽中學習。我在詩歌里聽到的聲音,它的音色、速度、位置,更接近我想在小說里實現的語調。
封面新聞:在你的小說里,春天、夜櫻等意象很突出。你自己有意識到嗎?
張玲玲:意象突出,是的。第一本書就標注了很多年份,甚至細化到幾月幾號。時間其實是種標記方式,確定你的事件節點,猶如浮標。第二本書模糊不少,成塊時間多了,所以季節成了一個象征。在南方,四季的界限其實并不那么涇渭分明,但你總能在植物、天色的細微變化里感到時序的輪轉。這種流轉就像月的陰晴圓缺一般,不因人的悲歡而改,有時你會因此種重復性絕望,但有時也會因此種重復性而感到深層的、持久的慰藉。至于櫻花,我不確定它是否比其他有季節意味的植物出現得更多。本來櫻花是一種尤為日本的意象,但這十多年,櫻花實際上已經成為江浙滬最常見的觀賞樹木,遠勝于桃、李、梨等更中式的植物。也即,它是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重要構成,盡管是移植、新興的。我尋找的并非陌異的事物,而是日常事物變得陌異、充滿情誼的時刻。
“全職進行文學寫作的想法是奢侈的,理解周圍同在寫作的朋友們的掙扎”
封面新聞:你曾任財經記者、編劇等職。你現在是專職寫小說。專職進行純文學寫作,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很不容易的。是怎樣的動力或者勇氣促使你做了這個選擇?你是怎么就開始寫起小說來了?
張玲玲:我很難說清寫作愿望的根本性原因,為什么寫?為什么想寫?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和才能、天賦毫無關系。天賦黑暗而耀眼,擁有者應該能識別出來,但我從未在自己身上目睹。我讀自己的小說時所感到的失敗遠大于可能的滿足。寫作本身需求的很少,在其他藝術門類里,它也是需求最低的。但同時,它和其他藝術一樣,全職的想法是奢侈的。我很理解我周圍同在寫作的朋友們的掙扎:想寫,無法寫,想寫,不能寫,在責任和愿望間艱難地博弈。因為到了這個年歲,你需要安頓的不只是自己。我無非對責任拒絕得更徹底。
回江蘇后,因寫作之故,我租在外面,沒住家里,我母親有時會來看我。我們坐在那間小公寓里聊天,面對她,我有時會陷入一種真實的失語,我說,媽媽,你快樂嗎?她說,我不,一點也不,你呢?我說,媽媽,我很幸福。我說的是真的,我因寫而倍感幸福,但我該怎么衡量、估算其間的代價:勞作的代價、身體的代價、經濟的代價,我付了一部分,還有人為之買單。我自認的幸福代價不菲,我自認的幸福也脆弱不堪,她看清我的執拗及注定的失敗,可我又該怎么說,媽媽,我無非是心甘情愿。
“天賦不是其來有自,而在日常勞動里予以夯實”
封面新聞:有哪些作家的作品對你的影響特別突出?
張玲玲:我喜歡的作者非常多,如果列出,將是一串長長的名單。我的感觸是,能學的僅僅是通用層面的,每個作者最迷人、最核心的部分你無法學習,那就是他們獨特的運行策略,滲透在每個詞語、句子之內。也許可以仿效一兩篇,但更多、更長的篇目你仍然得尋找、發明自己的方法。好作者教的是你如何成為自己,教你最大化發展自己。
真正打動我的,影響我的,不是技術典范,而是人生典范。愛麗絲·門羅給我的影響最大——她影響了很多人,我只是無數受益者之一。她在許多不利的位置得出強勢的結論,她示范了從普通主婦抵達卓越的可能,不輕視微小,不高估宏大,保持懷疑,也保持希望。天賦不是其來有自,而是在日常勞動里予以夯實。困頓時,沮喪時,我常讀幾個熟稔的短篇,總會有所收獲。
封面新聞:你的小說里人與人的關系,不少是愛情的關系。他們之間的來往、糾纏等等,在我看來,其實看到的不是愛情,而是當代人的一種心靈生存狀況。
張玲玲:我想,任何一段關系都有不同層次,層次之深淺取決于他們交出自己的程度。有時出于種種原因,其關系只能維持在較低層次上,所以一男一女之間,產生糾葛或其他,你只能說,這是一段兩性關系,而不愿上升到愛情層面。
封面新聞:寫小說需要故事素材,對你來說,搜集素材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嗎?未來你想寫出怎樣的理想小說?目前來說,寫作上遇到的困難是什么?會怎么努力去解決?
張玲玲:寫第二本書時我有短缺感,或者說自覺重復,但到了此刻,我想問題倒不是短缺,而在于對既定素材的理解,以及陌生材料未曾熟透。搜集不難,難的是為什么而搜集,搜集什么,以及對材料能了解到什么份上。我可能想先盡量寫好手頭的。寫作的人可能感受大致相同:理想是為理想,多因為得不到。且理想有其階段性,這個階段我希望情節、人物、結構更均衡、更豐滿,最好能提供一種更新鮮的小說美學。困難還是在上述問題。方法無他:多讀,多想,多寫,重要的是多寫。
小說在當下面臨的競爭是多樣的,不只是視頻、游戲
封面新聞:當下這個時代,人們的心靈世界因為網絡的助推,變得越來越短平快,不那么有耐心閱讀文字,尤其是嚴肅的文字。作為一個小說作者,你的體會、觀察、見解、看法是怎樣的?
張玲玲:無論我們如何高看嚴肅閱讀,但作為個人教育的實用閱讀,與出自審美追求的消遣閱讀,或出自娛樂目的的休閑閱讀,其實也很難真的分出高下。我很理解人們工作一整天,只是想輕松一下,睡一覺,喝一杯,打一局。打游戲的未必比閱讀的更焦躁。有些游戲文本還很精良,只不過動用的敘事系統不一樣。閱讀習慣的培養需要漫長的時間,它是一種訓練后的肌肉記憶,也許你得學會在孩童時,就得充分享受閱讀的趣味,在今天,對很多人來說,閱讀其實是痛苦的。我只能說,即便如此,閱讀仍然是值得的。
作為小說作者,我覺得我們最好認清自己的處境:你不只在跟視頻、游戲、工作競爭,還得和別的文本門類、小說類型競爭。在最窄的領域,你也得和同代作家、經典文本競爭。能分給你的時間和份額是極少的。所以我對每個花時間讀自己小說的人都心存感激。
封面新聞:現在大家都會經常提到一個詞“情緒價值”或者“情緒穩定”。如果遇到讓人感到沮喪或者憤怒的事情,你是如何保持清晰平靜的?
張玲玲:三十歲之前我不保持平靜。憤怒是因為你還有力氣,還有覺知。太早到達一種超脫的狀態不是什么好事,可能離人的位置,事實的位置,情緒的位置都太遠了。今天我們都說“信息繭房”,人很容易給自己構建出一個真空帶。但與此同時,人愈發脆弱,對于負面情緒的消化變得更難。我能學會的是,不針對任何具體的個人而憤怒,不對一星點碎片信息憤怒,一旦涉及具體處境具體語境,可能誰也不比誰更高尚,而我們判斷的傾側有時僅僅跟掌握信息的多寡有關。
封面新聞:你現在正在寫什么作品?平常一天的寫作和生活時間是怎么分配的?
張玲玲:我在寫一個長篇。除了睡覺、吃飯等,好像沒什么生活可言。有段時間我因為生活一詞,略覺困擾,后來讀到薩爾曼·魯西迪的訪談說,“作家有什么生活?”終于釋然了些。我不是說我總在寫,寫是一個長期狀態。在那狀態里,你做任何事的時候都心不在焉,總被另一個世界所牽動。你腦子里總是句子,而不是別的。
標簽:


眼紅AI熱潮引發反噬 “美版貼吧”執意對數據收費 用戶:都別玩了

伊一為什么被封殺知乎_伊一為什么被封殺-每日時訊

-
1
欠信用卡錢會連累夫妻嗎? 沒錢還信用卡了怎么辦?
-
2
天然氣多少錢一立方米?天然氣是怎么收費的?
-
3
什么是毛利?毛利怎么算?毛利的計算公式詳解
-
4
德國2月工業新訂單環比增加4.8% 為連續第三個月環比增加
-
5
還不上信用卡被限制高消費后有什么后果? 信用卡欠了三千會被起訴嗎?
-
6
特斯拉:2022年得州超級工廠的員工人數增加了兩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