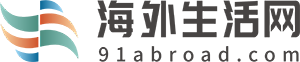他們,走過歲月 依然青春-天天新要聞
杰茲·斯科利莫夫斯基
第2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今日閉幕。在本屆電影節里,盡管佳作紛呈,但是給人們留下更深印象的,卻是兩位導演:一位是已經離去的謝晉導演,第一屆上海電影節金爵獎評委會主席,今年是他的百歲誕辰;另一位是本屆金爵獎評委會主席杰茲·斯科利莫夫斯基,今年已經是85歲高齡。
 (資料圖)
(資料圖)
謝晉,是中國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導演之一,也是中國第三代導演的代表;杰茲·斯科利莫夫斯基,波蘭新電影的代表人物。人們之所以關注他們,并非僅僅因為他們曾經對電影藝術做出的貢獻,更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探索精神、敢于創新的勇氣,以及不輕易低頭的藝術品格,恰是當前中國電影所亟須的。
謝晉在其倡導下誕生上海國際電影節
謝晉導演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中,留下了36部優秀的影片,他對歷史、社會、人性的關注與思考,影響了無數觀眾。2018年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謝晉被授予“改革先鋒”的光榮稱號,也是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國導演。
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滕建勇在致辭中表示,1993年正是在謝晉導演的倡導下,誕生了上海國際電影節,“由謝晉先生本人親自擔任金爵獎評委會主席,旨在為國內外的電影人,無論是知名與否,搭建一個專業的、包容的、國際化的電影交流平臺。也正是因為謝晉先生敏銳的藝術嗅覺和精益求精的專業標準,上海國際電影節自第二屆起就被認定為國際A類電影節。30年后,我們再次因電影相聚于此,更不應該忘記謝晉先生在推動上海乃至中國電影行業發展、引領中國電影國際化方面做出的巨大的貢獻。”
“金杯銀杯不如觀眾的口碑”
謝晉始終以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為切入點,一句“金杯銀杯不如觀眾的口碑”道出了他為人民創作的理念。導演、編劇、電影監制黃建新在事業起步階段就得到過謝晉的鼓勵,但更讓他難忘的,還是老百姓對謝晉發自內心的認可——2008年謝晉去世,黃建新趕赴上海參加追悼會,全國各地的影迷自發趕來送別的場面讓他格外觸動,“那個瞬間,我心里感受到了崇敬”。
導演、監制、香港電影導演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永遠榮譽會長吳思遠則難忘于1992年在香港召開的,由海峽兩岸暨香港電影人參加的第一屆“電影導演研討會”。這場由謝晉、吳思遠、李行三位導演共同推動的研討會,開啟了眾多影人的交流與合作,為中國電影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吳思遠的記憶中,當時謝晉的發言就深深感染著每一個人,“我還記得他的金句——‘能留下來的就是好電影’。現在來看,謝晉的電影留下來了。”而在見證中國電影飛速發展之后,黃建新也一再感慨謝晉對中國電影產業的推動作用,“尤其是他在拍攝《鴉片戰爭》時取景橫店,從客觀上助推了橫店影視的起步與發展。”
斯科利莫夫斯基進入電影領域純屬意外
杰茲·斯科利莫夫斯基除了是導演,還是畫家、樂手、作家、詩人、演員、拳擊手等。聽到這些頭銜,斯科利莫夫斯基笑了:“我要稍微糾正一下。我是一個爵士樂團的鼓手,但我打得很差;我也當過拳擊手,不過是業余拳擊手,在拳擊生涯中的比賽有一半都是輸的,所以我也不是好的拳擊手;說到詩人,我的詩歌也發表過,只不過是刊登在發行量很小的刊物上,真是不好意思。所以,這些都不值得給予美譽。只有制作電影才是我真正走進大眾視野的唯一的機會,能夠真正將我變成一個藝術家。當然我覺得我還是挺幸運的,進入電影行業,對我來說非常順暢,而且我也一直扎根在其中。”
斯科利莫夫斯基進入電影領域純屬意外,波蘭電影《灰燼與鉆石》的編劇寫了另外一部影片的劇本,但不是特別滿意。他給斯科利莫夫斯基看了自己的劇本,當時還在忙其他工作的斯科利莫夫斯基,晚上花了五六個小時對劇本進行了調整,第二天這位編劇看了之后表示“非常滿意”,并力邀他加入自己作品的劇組。
不久后,才剛剛進入電影學院幾天的斯科利莫夫斯基又收到了一個特別的邀請——當年的波蘭奧組委希望請導演拍攝一部關于拳擊手的短片。這部短片后來在布達佩斯獲獎,斯科利莫夫斯基也開始了第一部長片《輕取》的拍攝。至今,斯科利莫夫斯基還慶幸自己的選擇,“我的職業生涯開始得這么順利,是因為我本人在那個時刻就是個做好了準備的電影人。”
曾“退圈”成為畫家離開后發現仍熱愛電影
拍出《輕取》之后,斯科利莫夫斯基把這部作品和自己學生時期拍攝的長片作品,一起送去了紐約的一個電影節,結果他聽到了很多人在贊嘆,東歐來了個有著獨特審美風格的天才。
當他在電影學院的同學們還在學習變焦的用法,通過這個技巧拍出汽車飛馳的效果時,他已經在采取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了——他用長鏡頭來呈現這樣的效果。讓眾人驚艷的《輕取》,甚至只有28個鏡頭,他使用的“一鏡到底”手法,后來被很多著名導演效仿。
斯科利莫夫斯基坦承自己至今一共拍了將近二十部電影,其中有三四部很差,“甚至可以說是很爛,比如我不太喜歡的電影是《急流的春天》,有時候也翻譯成《春潮》,有三部我最不喜歡的電影,都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這樣的不滿意,甚至導致了他后來的“退圈”。
他當時“決定不再拍電影”,希望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繪畫中去。他在繪畫方面的天賦,讓他在美國和歐洲都開始小有名氣,畫作也賣得很好,甚至獲得了一些國際比賽的獎項,“這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年輕的藝術家了。”
形容自己“電影職業生涯像蛙跳”的他,在離開十幾年后發現了自己對電影仍有熱情,于是他在給自己定下一個“不拍爛片”的要求后,重新回到了電影行業。“在我重回電影行業后的四五年里,我拍了一些挺好的電影,包括《必要的殺戮》《11分鐘》等。現在我特別推薦我最新的電影《EO(驢叫)》,我自己覺得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拍得最好的一部電影!”如今已經80多歲高齡的他,說這部作品讓他覺得自己“依然是一位年輕的導演”。
雖然說“鼓勵觀眾去看”,但如今的他,已經不會去迎合觀眾了。他曾在一次采訪中說,“如果一部電影太完美,就不需要觀眾、也不需要任何影評人的評論,它應該直接進入到觀眾心里。”在上影節的論壇上,他也表現出了“少年心性”:“我會挑戰觀影人的聰明才智,我不想把所有信息都按照順序標注好編號再告訴他們,而是用一種非線性的方式展示給他們,這樣所有觀眾都會對電影有自己的解讀,觀眾才會有一種滿足感,才會覺得自己在心智上、在精神層面上和電影創作者有所交流。”
本組文/本報記者肖揚
統籌/滿羿
標簽:


天天即時看!現場直擊!關系江陰1.4萬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