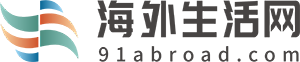對談|黎紫書&許知遠:擺脫雨林書寫,重新構筑異域世界
在潮熱的赤道雨林,馬來西亞華語文學以獨特的奇異姿態生長著。馬華作家黎紫書帶著她的寫作故事,于最近來到了中國并將舉辦系列活動與讀者們進行分享。
現場
最近,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聯合單向空間舉行“歡迎你來到我的世界——黎紫書作品分享會”,《流俗地》作者黎紫書和作家許知遠,共同走進馬華文學的世界。
 【資料圖】
【資料圖】
黎紫書
曲折的歷史、語言的隔離、邊緣的身份——在文學環境貧瘠的馬來西亞,華文寫作者一直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黎紫書做過小學教師、洗碗工人、鞋店銷售、記者,辭去記者這份工作后,她決心專心做個作家。作為七零一代馬來西亞華人作家的代表,黎紫書以短篇小說起家,題材豐富多變,充滿異域風情。2021年,黎紫書攜長篇小說《流俗地》歸來,故事以盲女古銀霞的人生為主線,描繪馬來西亞怡保小城里的眾生百態、俗世悲歡;作者以詩意的文字,娓娓道來馬華社會近五十年的風雨悲歡與人事流變。
《流俗地》
在《流俗地》《告別的年代》《野菩薩》中,在黎紫書構建的異域世界里,可以看到她對歷史的回望,對現實的關懷,對身份的尋求。
“試圖擺脫雨林書寫”
在那季風吹拂的土地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兀自生長。近年來,張貴興、黃錦樹、黎紫書等馬華作家的文學作品也相繼在中國大陸出版,掀起了一股“馬華文學熱”。與前輩們不同的是,黎紫書試圖擺脫雨林書寫,建構起世界性的文學書寫方式,已經成為馬華文壇甚至整個中文世界的一道別樣風景線。
黎紫書從未接受官方嚴格的華文教育,在談及如何從怡保走上文學之路時,她說道,“整個家里面只有我一個人喜歡看書,我又是一個特別孤僻的孩子,我看書只要拿到手,打開它就一定把那個書看完,不管我看不看得懂、不管我喜不喜歡,我只要打開它,就會珍惜每一本書,會把它看完”。
對黎紫書影響巨大的,是魯迅的短篇小說《孔乙己》,雖然她所在的文化背景與魯迅小說中的背景不同,但她依然能從小說中感受到文學的力量,逐漸找到喜愛文學的原因。這種閱讀體驗,使得她更喜歡短小的微型小說,更追求“把五分鐘的閱讀留存在生命中五年、五十年”的效果。黎紫書對中文世界的熱愛是完全自驅的,從《唐詩三百首》到溫瑞安等人的武俠小說,她嘗試用粵語這一媒介勾連起自己與華文的聯系,用古典文學的韻致構建起對中文世界的文化想象。
對在北京長大的許知遠來說,他想象的馬華作家和這些作家所代表的南方世界是潮乎乎、霧蒙蒙、黏稠稠的,但黎紫書干脆利落的語言方式給他帶來了全新的感受。許知遠問道:“對于一個20歲出頭的怡保年輕人,成為一個作家是一種自殺性行為嗎?你對‘馬華作家’這個身份定義有什么感覺?”
在馬華文壇這個邊緣的小圈子里,黎紫書從未在年輕時向他人說過要當作家,她的寫作純粹來源于熱愛,“在這個小小的寫作圈子里,今年你拿獎,明年我拿,大家輪著拿,我們就很滿足快樂了。馬華文學世界里也只有這一小撮人,他們是你的同行,也是你的讀者。”因此,為了工作穩定,黎紫書在成為作家前一直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寫作著。
黎紫書從35歲后開始嘗試當一個作家,她覺得自己是幸運的。24歲第一次出道,就斬獲馬來西亞文學最大獎項的花蹤文學獎小說首獎;第二年就在中國臺灣獲得聯合報文學獎的小說首獎;之后,黎紫書基本每年都能獲得各種大獎,“不僅僅在馬來西亞這個小池塘里游泳,現在已經泳到東海去了,我們那邊俗語是到公海了”。
流俗世界里的黎紫書
十多年的新聞記者工作讓黎紫書收獲了多樣的人生體驗。報道車禍新聞、采訪諾貝爾獎得主、訪問月餅鋪老板,她報道的題材、采訪的人物觸及社會不同的層面。于是,在《流俗地》里,黎紫書游刃有余地處理著小說里各種不屬于自己生活圈子的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如果沒有那十多年當記者的生涯,今天的我不可能寫出像《流俗地》這樣的小說”。
在離開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后,黎紫書印象中的怡保變得遙遠起來,可能因為遙遠反而變得清晰起來。她來到北京,又去過倫敦,還去了德國、以色列、美國的許多地方,一次次遷徙,見證過無數地方的時歲變遷,但當每次回到怡保時,她都發現它的面貌從未變化,“年輕人對它絕望的地方,正是我這種老人最想念的地方”。
在離開馬來西亞時,黎紫書開始構思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十多年前,為了證明自己是一個能寫長篇小說的小說家,她在書里運用了復雜繁復的結構形式。到了十多年后再寫《流俗地》時,她選擇了返璞歸真的、簡樸的,但難度比創作《告別的年代》大了許多的小說形式,“因為要把所有情緒都融化在形式里,它是在文字底下的形式。你看不見那個形式不代表沒有,是作者很努力把形式本身融在文字底下。作為一個作家,我不再執著你看不看到、你認不認可,而是這個小說這樣寫,且應該只能這樣寫。這就是創作《告別的年代》和創作《流俗地》時的差別”。
在這十多年中,黎紫書完成了多篇微型小說的約稿。盡管嚴肅文學對微型小說等閑視之,但黎紫書卻在思索著“怎么把這一千字的小說寫好,寫成文學,寫成具有文學高度和深度的作品,對我是非常重要的訓練。微型小說訓練使我懂得舍棄,讓我每使用一個文字時都要求自己反復推敲,這是我需要的嗎,作用是什么”。
“這些微型小說的寫作訓練讓我后來寫《流俗地》的時候,對小說創作有了這樣的想法:我是為了成全這個小說而存在的,不是我企圖用這個小說成全我自己”,因而她將自己的心血全部傾注進《流俗地》,沒有一個字懈怠,“我可以把自己放小或者放得更低,告訴自己,我寫這個作品是為了成全這個作品而存在”。
許知遠問道:“最初寫作《流俗地》的理念是怎么出現在腦海中的?你的創作習慣是會在腦中看到人物走過來,還是能在寫作時聞到怡保的氣息、見到傍晚的夕陽?”
黎紫書坦言自己不喜歡在落筆前做提綱和提案,有了隱約的概念后,她便會在腦海中不斷將概念醞釀成熟,最終真正落筆寫作的時間大概只有八個月。《流俗地》里最先向她走來的角色是銀霞。盲人和出租車調度員這兩個看似沖突的身份,使銀霞在存在偏見、文化紛雜的馬來西亞世界里承擔著訴說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這一更重大而深刻的意義。
黎紫書同意許知遠所說的“寫作的這八個月就是在小說世界中行走的八個月”,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創作的世界是虛構的。創作《流俗地》的這八個月給她帶來了身心的巨大痛苦與折磨,但她始終堅持不將自己的這份痛苦狀況帶進小說中,小說應該保持它自己原有的節奏。
《流俗地》的節奏也是黎紫書比較得意的部分,小說主角會自動推進自己的結局,而她是這個小說世界里的一個親歷者,她好像真的認識書中的細輝、拉祖、銀霞,“所以當我完成這部小說以后,我是真的覺得可以跟這個世界說拜拜了,我明天可以不回來了,有一種非常大的成就感,有非常大的放松”。
重新構造一個怡保的世界
怡保的發展原地踏步,因而塑造了怡保人不太著急的個性和慢悠悠的生活步調,所以盡管見識過北京、香港的城市生活,黎紫書依然說,“可以在不緊不慢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步調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我們怡保人是這樣的一批人。這個原因也是我之所以會喜歡怡保,一直想回到怡保老去的原因。不管文學的世界怎么變化,讀者還看不看我的書,我都會寫下去。不管你看不看,我還是會用自己的方式步調寫作,我這一點是相當怡保人的”。
怡保所代表的多樣文化證明了它曾經風光、繁華過,但錫礦業的沒落使得怡保若想有所發展,就不得不發展旅游業。“怡保人就是那種,明知道旅游能夠帶動經濟,可是心里面還是覺得不要發展,游客不要過來。我們還是想回到可以慢悠悠跑到舊街廠,坐在破落的茶室里面吃很便宜又好吃的雞絲粉,過著老生活”,黎紫書之所以選擇留在怡保,就是想過這種生活。怡保的特殊環境能培養出專心的人,沒有世俗功利心。
黎紫書小說中的怡保又在現實的怡保上蒙上了一層夢的幻境。在《告別的年代》中,黎紫書展現了精彩的夢境書寫,尤其是主人公關于悼念亡母的充斥著“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苦悶夢境,黎紫書甚至借助主人公之口直指其對夢境的感知與思考,“你以為夢本身是蟻穴那樣的國度,里面溝壑縱橫,蜂窩狀的小房間櫛比鱗次,你永遠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出口在何處”。在《流俗地》中,黎紫書延續了《告別的年代》中對于夢境的癡迷式描寫,她用大量篇幅打造勾勒各式人物的夢境空間。《流俗地》中出現的第一個夢境是細輝搬離組屋后,在昏暝而燠熱的夢境中踏進理發室找尋拉祖下象棋。銀霞也做過相似的夢,她的夢除了人聲、塔布拉、薩朗吉、巴布打鼾聲、電風扇搖頭聲、麻雀啁啾的聲音記憶外,還充滿理發室的氣味——焚燒檀香、茉莉花、酥油燈、雞蛋花、叫不出名堂的香料、薄荷味剃須膏等。這些夢境重構了一個新的怡保。
標簽:


女貨車司機月入2萬在車里住2年